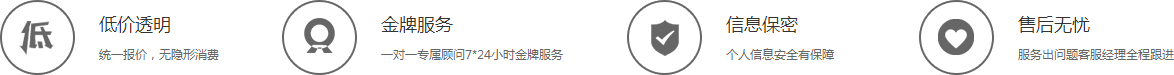发布时间:2024-12-01 热度:
走出财政危机的建议
制定财政危机解除计划,首先要解决燃眉之急,然后从长远来看,追求合法性最大化。这就提出了如何协调短期政策运作和长期制度建设的问题,这是对“诺斯悖论”的挑战。我们认为,以下三项建议的实施结果有望与我们的目标耦合。
1.出售部分公共资产
我们(魏凤春于洪欣2001)在讨论社会保障基金筹集方法时提出了一个框架:出售部分公共资产可以解决社会保障基金债务问题。养老金历史债务是政府最大的隐性债务,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即期债务支付压力。因此,出售公共资产可以满足上述计划的第一个要求,即短期经营可以解决紧迫问题。政府不仅可以增加收入,还可以减少对国有经济的补贴。此外,还有更长期的利益。
首先,出售资产融资不仅可以筹集资金,还可以成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的手段,将宏观总量政策与微观结构性改革相结合。根据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确定的“进退”方针,对国有经济进行根本性改革和布局调整,大幅缩小战线,有利于解决政府越位和缺位问题,也是追求合法性最大化的唯一途径。
其次,当政府难以选择国有企业的“输血政策”和“改革政策”时,维持前者的资本成本过高。因此,在给定银行制度风险不增加的约束下,只有出售国有企业资产,才能真正解决以国有企业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制度矛盾。国有企业20年改革的“试错”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出售的资产必须有价值,应该是“美女先结婚”。至于卖什么,卖多少,这是一个具体的操作问题。这也是国有股减持一段时间以来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的理论依据。
第四,居民存款余额已达7万多亿元。资产管理公司持有的国有不良资产在国际市场上的顺利销售,说明购买力不是问题。具体操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意识形态问题和定价问题。如果以真实价值为参考,“世界上没有卖不出去的商品”。
2.完善非国有经济制度
公共资产的出售可以看作是对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进退关系的动态描述。公共资产的出售首先是为非国有经济进入高于平均利润率的竞争性行业创造空间,并为非国有经济的金融剩余提供出路。这是由于财政压力,政府没有积极改善,因为国有经济的退出需要非国有经济的承担。国有股减持的高定价可以反映这一点。
这里提出的制度完善主要是指政府的主动改革。原因可概括如下:
首先,虽然我们不同意以下观点:所有制形式与协调机制之间存在“自然”对应关系,即社会主义国有制与行政协调之间的薄弱联系,国家试图使公有制与市场机制兼容是徒劳的,“第三条路”不起作用(科尔奈1992)。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国有经济反复试错的结果和非国有经济的强大活力,更现实的是面对非国有经济萎缩导致经济增长停顿或“危机”的可能性。范刚(2000)曾提醒说,即使非国有部门很大,剩余收入也很大,如果国有部门得到更大的补贴,增长停顿也可能发生。
其次,中国20年的改革已经进入帕累托改善的状态。培育非国有经济必然会收缩国有经济,面临短期内社会不稳定风险增加的考验,不可避免地面临现有权力和利益集团的诸多阻力。因此,作为公民代表的国家应该对消除改革的阻力负全部责任。这也意味着另一个层面,中国的加入可能会减缓政府消除阻力的步伐。在内部改革的背景下,外部影响将给我们的市场化进程带来机遇,但如果我们只依靠外国援助而忽视自力更生,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很难维持。我们一再强调,非国有经济的增长是确保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提,因此内部改革将更加重要。
在我们看来,政府需要积极改革的几个关键点(当然,非国有经济本身也需要改善)包括:保护私有产权、清理历史遗留下来的未知产权、鼓励和允许私人投资、鼓励私人金融、银行信贷、资本市场国民待遇等。
3.财务管理技术改进 前面的两个建议是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的举措,而要真正地实施,则尚需时日。利益集团的阻挠可能会使其难产或流产,因此,它是远水。近渴的解除还依赖财务管理技术改进。技术改进的目标应该以减支为主,而不应该注重于增收。费税改革、政府采购、国债资金的使用、对国企补贴的取消、行政开支的缩减、政府资金的效率、公共决策的配合等等都可以暂时地缓解财政的窘境,但它并不能根本地使财政远离危机。